阳寿: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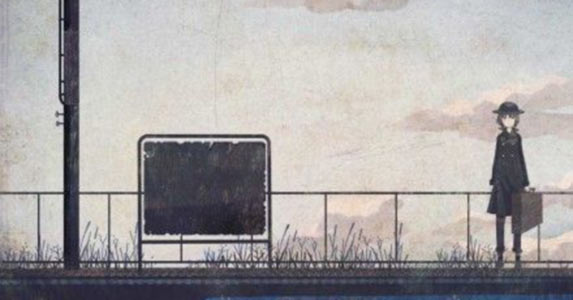
1
范岳用屁股怼开对面502宿舍的门,拍拍腋下夹着的篮球,一贯粗豪的声音还是那么震耳欲聋,“走啊哥几个,打球!”
平时范岳这么喊,一般会有两种反应:或是响应者众,那一般都是午后傍晚;或是臭鞋臭袜子下一秒就扔了过来,那是早晨。
范岳才不管那么多,他心里打篮球是顶天重要的事情,才不会因为谁通宵玩游戏、谁昨晚上出门约会,而改变他日复一日的邀约。
可此时宿舍里虽然人差不多全齐,但静悄悄的,其他几个人看是范岳这个二百五进门,把窝在手心的烟都亮了出来,但没人说话。
“抽什么好烟呢?抽得这么严肃?你们放心,我绝对不和我们寝室的说。”范岳嗓门降了下来,硕大结实的身躯做起鬼鬼祟祟的动作分外可笑。
他回头看了看宿舍门,慢慢关上,从其中一人手里硬抢过来半根,转着看了看,迷惘地抬起头,“抽根红塔山也能让你们这德性?”
“奚志远休学了。”宿舍里老大淡淡地说,手里的烟头忽明忽灭,“确诊了重度抑郁,医生说他情况很危险,必须住院治疗或者在家休养,他就回去了,我们正商量让谁去看望他呢。”
范岳的国字脸罕见地没了笑模样。
2
中海市某个小区外,范岳看着手机上标注的地址,在深一脚浅一脚的雪地里艰难跋涉。这个城市刚刚下了一场历年少见的大雪,大地银装素裹,好看了很多,可对于一个陌生的外乡人,找起地址来也更难了。
范岳路过一家算命店,眼神茫然地扫过店门旁边的玻璃,店里书架上放着好几本大部头,如果是别人可能看不见是什么书,但范岳视力足有五点零,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几本书脊冲着店外的书都是心理学书。
他从茫然中回过神,推开店门走进去,客客气气地问了那穿着厚羽绒服、仿佛豆芽菜外面罩了个龙眼壳一样的干瘦老人几句,弄清楚奚志远家里地址、谢过之后推门要往外走。
那老人突然叫住范岳,眯起眼看了看他,“小伙子,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再回来一趟,我师叔祖也许能帮到你。”
3
奚志远家很大,也很空旷,暖和是真的暖和,但范岳看着这家,总觉得和自己那虽然有点乱糟糟的家相比,少了一点什么。
奚志远的母亲亲切地接待了请假来看望奚志远的范岳,客套话说完后,她叹了口气,“实在不好意思啊,范同学,志远他现在在睡觉,他最近一天要睡二十个钟头,大夫说他这个毛病就这样……”
“没事,阿姨,我可以等他醒过来。”
范岳已经尽量压低了嗓门,但声音还是被刚睡醒的奚志远听到了,房门一响,奚志远笑着走出来,冲范岳胸膛就是一拳,“可让你逮着合法逃学的机会了!”
范岳嘿嘿傻笑一声正要回嘴,却看着才半个月不见就胖了不知道多少的奚志远,突然想起什么,拽着奚志远进房门,“老奚你来,我问你个事,阿姨你别管我们了,我们自己玩啊。”
进了房门,范岳关上门坐下,眼神严肃地看着奚志远,“老奚,你老实点回答我,你是不是因为我之前那回说你,才落下这个毛病?”
原来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新学期刚开学,范岳又一如往常地在502寝室侃大山。奚志远曾经提过一嘴,自己最近情绪很差,身体还总是莫名其妙地疼,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他自己对照网上搜索的结果查过,好像是抑郁症。
那时候,嘴没遮拦的范岳当时就笑出了声,“什么抑郁症,我看你就是没女朋友给憋的,要不就是矫情!你说现在这些人也是,一个两个地,不弄点精神病在头上就是不行,什么密集恐惧症啊,幽闭恐惧症啊,我看全是装的,打一顿就好了!”
当时奚志远只是笑着看了看范岳,没有回话,几个月后就办了休学回家。这可让听到消息的范岳良心难安了好几天,他翻来覆去地想,怎么想都只能确认:他奚志远得了这个病,很有可能是自己的锅。
他范岳虽然不算很聪明,但自己老爹从小用拳脚棍棒教给他的道理并不难记:做男人,挨打站稳,错要承认。
所以他特地请了假来找奚志远,其实是想认个错。范岳想得很好:既然是自己犯的错,那自己就来敞敞亮亮认了,他奚志远要打要骂都随便,即使要他去学校大礼堂念悔过书,他也认。
这几句话范岳在火车上来来回回寻思,这时候也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话音未落,就看坐在范岳对面的奚志远,又露出了那天晚上的微笑。
“范岳啊,”奚志远脸上有一种范岳完全不明白的表情,他看着范岳,仿佛每说一句话都在用很大的力气,“精神疾病其实很大可能是脑部病变,所以这事和你无关,也不是你道个歉能治好的。我现在好歹按时服药,自杀倾向也好,抑郁症状也好,还是控制得不错的,只不过副作用让我没法学习,我也只能先呆在家里,休学了事。你放宽心,难得来一趟中海,不如多住两天,好好玩玩。”
他脸上,那种苦涩的笑又出现了,“可惜我没办法陪你打篮球了,我现在吃着药,总是视力模糊,还嗜睡,你看我都胖了多少斤……”
范岳看着奚志远,重重点点头,用力拍了拍奚志远的肩膀,“行。”
4
算命店里,王山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雪花纷纷扬扬落下。刘文轩谄媚地前后服侍着他,端茶送水递橘子,半晌才讪笑着开口:“师叔祖,腊八粥……”
“你不能去。”王山一句话就堵死了刘文轩,他气哼哼地回头走向自己常坐的沙发,“妖怪聚会而已,为啥我不能去?”
“你是真胆大,那群妖怪光喝粥肯定不满意,弄点配粥的小菜再正常不过,你虽然七老八十皮糙肉柴,但备不住就有爱啃肉干的啊。我又不能一直护着你,作什么死,不能去就是不能去。”看到王山严肃起来,刘文轩这才悻悻地打消了念头,他转过头看着门外,一个浑身是雪的人刚巧这时手抓门把,推开了算命店的大门。
“大爷,我借你这儿的心理学书看看行么?”那人正是范岳,他在门外扑打几下身上的雪花,咧开嘴笑着。
“行倒是行,可是你要借书干什么?”刘文轩端起架子,捻着自己颌下长须问。
这可正对了范岳胃口,他现在是真憋得难受,正想找个人说一说。
半小时后,刘文轩看着坐在对面的范岳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确实可以听你同学的,玩两天回学校去了。抑郁症目前……医学界还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终生服用药物抑制病情。不过前几天忘记哪个期刊上有个研究,说是海那边实验室里出了重大进展,可是从研发到研发成功到民用,没有十年二十年也看不到头……总之靠医院,目前就算是最好的治疗办法了。哦对,你让你同学家长多看着他点,刚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会有一定程度的自杀倾向,总之,就是麻烦。”
刘文轩突然回头看了看正坐在沙发上、低头玩游戏的王山,贼笑起来,“可是我知道有个人,肯定有办法治你同学,而且是根治,彻底治好那种……就看你能不能求得人帮你了。”
王山叹了一口气,将手机放下,无奈地瞪刘文轩一眼,手伸进了裤兜。
5
范岳看着眼前的火光消失,抓着沙发的手这才放松下来,眼神中的将信将疑已经彻底变成了确信,“这契约……这契约竟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不过既然是试用版,只用了你三个月寿命,那么换来的效果也不多,只有三次。”王山抓起范岳的胳膊,指着他手腕上那突然多出来的三叶草刺青,“一片叶子换一次,用的时候和那人必须身体接触,心里默念这契约的福利‘开心’,再去按着你那同学的头,心里默念把你借到的开心给他,就完事了。”
范岳眨眨眼,“这契约的福利叫开心,所以就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开心?那我直接把我自己的开心分给奚志远,不就得了?”
王山解释道:“这契约你自己用不行,其实还有另外一张自己就能让自己开心的契约,可是那张不在我手上,不然事情更简单,把你同学领来,签完了事。现在这张试用版,只能让你以身为桥,借别人的开心渡给你同学,你自己的用不了。”
王山的脸严肃起来,“一定要找你觉得最快乐的人,借他们的‘开心’给你同学才有效。”
6
第二天,范岳起了个大早,拿着奚志远给的联系方式,出了奚志远家的门。
昨天晚上他苦思冥想,半晚上终于想到了答案:不是说,有钱人的开心,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么?那他找个最有钱的人,去借他们的“开心”不就得了?
可范岳并不认识什么有钱人,也幸好他还住在奚志远家,范岳找了个由头,对奚志远撒了谎,说自己请假出来的名头就是做名人调查。奚志远听范岳说要找很有钱的人,就跟母亲要了一张名片,是奚志远父亲供货的、中海数一数二企业的大老板。
见面的过程出乎范岳意料地顺利,范岳在中海市中心那栋用这个大老板的姓氏命名的大厦里拿着名片一路连蒙带骗,夹在前后两拨会见这名大老板的客人中间,竟然让他闯到总裁办公室门外。
但办公室门外的大姐也不是吃素的,她看着一脸学生样的范岳,开口就问:“这位先生,请问您预约的名字是?”
范岳冷汗当时就流了下来:他有个屁的预约!要是拿着名片等预约,那他这学期课可以不用上了!关键时刻范岳脑中灵光一闪,鼓足了劲,在总裁办公室门口大吼一声:“杭州马总派我来的!”
总裁办公室的门立刻开了,那一脸富态的中年人打开门四处张望,“哪个马总?难道是……”
范岳赶紧冲过去,一个转身晃过伸手拦他的秘书大姐——他从没觉得在篮球场上锻炼出的过人技巧如此有用——伸手握住这位大老板的手,一边心中默念“开心开心开心”,一边嘴里不住往外冒胡话:“孙总是吧,我是杭州……呃……天边太阳伞公司下属……呃……传……直销事务部马总派来的,您有没有兴趣给公司每个人配一把我司出产的太阳伞?”
几分钟后,被两个虎背熊腰的保安客客气气地请出门外的范岳,嘿嘿笑着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腕上三叶草刺青的叶子已经没了一片,志得意满,“小事一桩!”
他赶紧打了个车,回到了奚志远家,和奚志远母亲打了个招呼,就走进奚志远卧室里。手轻轻按上奚志远的额头,冰凉的手让奚志远哼了一声,睁开眼看看范岳,眼中满是木然,一言不发,闭上眼睛又睡过去。
范岳闭上眼睛,心中默念:把我借到的开心给他!
他浑身一震,眼中突然浮现过好多幻象。
刚才和他握手的那个大老板的人生仿佛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浮现:少年父母双亡,从小靠给人卖油条走街串巷糊口;稍微大一点,有了自己的小生意,被人举报投机倒把关了几年;等放出来,有了案底,公职一概不录用;万般无奈之下又做起小生意,没想到改革开放,政策改变,只要吃苦耐劳就有出头的机会。他是苦出身,既然吃得苦中苦,给个机会,怎么不能成为人上人?
结过三次婚,前两次离婚都因为他一心忙事业,家庭分崩离析;生过好几个孩子,没一个能接下家业的,花起钱来倒是个顶个地厉害,还会嘲笑他“没品位”“只知道打几万一把的麻将”。
但他根本不喜欢打麻将。可是,人情往来总要做的吧?
自己那些老同学,只懂趋炎附势想分一杯羹的玩意儿自不必说,那些对自己真诚的,也因为他的身价地位而思虑甚多,怕被认为和那些溜须拍马的同学一样,和他交际是为了他的钱,而故意远离了自己。
幻象来来去去,好像是在寻找这个大老板人生中最开心的节点,最后却定格在这大老板很小的时候:
那是很普通的一天,大老板那时候还是个小屁孩,衣服上的补丁不比别人少。他和同学放学以后回家,发现父亲今天提早下了班,去排队凭票买了一斤猪肉,母亲给他做了一道红烧肉,父母俩几乎没动筷子,看着他把红烧肉就着糙米饭全吃了下去。他把菜汤倒进米饭里,扒了几口,透过昏暗的煤油灯,看着桌对面正含笑看着他的父母,只觉得那是他人生中最开心、最快乐的一天。
可是范岳知道,第二天,这大老板的父母就意外身故了。幻象中,大老板父母慈祥微笑的脸慢慢黯淡下去。
奚志远痛苦地哼了一声,范岳手慢慢缩回,轻咦一声,擦掉脸上不知何时流下的眼泪。
他走出奚志远的卧室,回到客房闷闷躺下,半晌才狠狠捶了一下枕头:有钱人快乐个屁!
不行,我得找到真正快乐的人。范岳用力想着,陷入梦乡。
7
天亮了,范岳茫然出门,不知道该去哪儿,该找谁。
他在中海市中心来回晃悠,看着街上的行人,也不知道谁才真正快乐,突然范岳拍拍脑袋,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刘文轩。
“刘大爷,你帮我问一下王半仙,小孩,特开心的那种小孩是不是也能用?”范岳的嗓门一向很大,听到这话的路人一瞬间齐齐回头看着范岳。
电话那头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跟他说,小孩不行,心境不稳,必须得是成年的大人,还得是一直很开心的那种。”
“听到了听到了,麻烦你们了啊!”范岳挂上电话,看着瞪视着他的路人,在身上摸索两下,忍不住瞪了回去。但众人不但没有被他高大的身形吓到,反而渐渐围了过来,还有一个姑娘打起了报警电话,“喂,110么?我报警,这边有个人好像要对幼儿园小孩……”
范岳扭头就跑,他的眼角余光瞟过街边的幼儿园,心中恍然大悟:娘的,在幼儿园门口,我特么都说了些啥!
常年打篮球锻炼出的脚力终于让他跑出了自发见义勇为的群众的围堵,他在小巷子里呼哧带喘,心想自己这下短时间是没办法出现在市中心了。
他鬼鬼祟祟地溜着墙角,迈步上了刚才用手机叫的网约车。
司机看是个体育生模样的大学男生,也没了忌讳,啪一下打开电台。电台里正播放着脱口秀,几个网络老段子在电台里那人妙趣横生的演绎下活灵活现,不止司机,连一直皱眉盯着窗外的范岳也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他突然一拍大腿:对啊,找喜剧演员啊!
范岳赶紧掏出手机,查看一下中海今晚的剧场演出,订了两张票,又打电话给奚志远,“志远,哦阿姨好,你跟志远说一声,今晚让他和我一起来听涛大剧院玩,别老在家睡觉了!”
当晚,剧院里笑成一片,范岳哈哈笑着回头看奚志远,发现奚志远也在微笑,感觉事情十拿九稳:等会儿我去后台堵个大腕儿,把他的幽默细胞给你渡一半,老奚别怕,你很快就有救了!
演出结束后,范岳捧着门口买的鲜花,拉着奚志远,在后台三拐两拐,找到了他看中的那脱口秀表演者的化妆间,礼貌地敲门,献花,范岳看着那表演者的脸,犹豫了一下。
那表演者不过四十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看到有热心粉丝来献花,笑得也很开心。可是范岳总感觉这眼前的笑星的表情,十分熟悉。
可是行动总比想法快的范岳,手已经伸了出去。
握了手,范岳说了几句恭维话,偷偷低头看着手腕的刺青,只有一片叶子了。奚志远只是在旁边静静站着,那笑星大哥礼貌地回着范岳的话,趁范岳去化妆间里放花的间隙,轻声和奚志远说了两句。他们说什么范岳没听见,也根本不在乎,出了化妆间的门,范岳拉起奚志远就走,“走吧哥们,咱们还有正事!”
找了一家快餐店,范岳看着眼前的奚志远,手特别自然地放在他额头,“你身体还行吧,没发烧?刚才那笑星跟你说什么了?”
“没……刚才那大哥其实就是问我最近吃什么药……呃!”奚志远话说到一半,头咣当一声摔到桌子上,看样子好像是睡过去了。范岳嘿嘿一笑,他刚才已经默念把借来的开心渡给奚志远,奚志远有这么一出,他早就料到了。
接下来接踵而至的幻象,范岳也一一看在眼里,这幻象自然是那笑星的记忆。但只看了一会儿,范岳就觉得不对。
这笑星除了在剧场表演的时候,竟然从来没笑过!
一瞬间晃过眼前的许多痛苦记忆让范岳皱起眉头,他从没想到,一个以逗笑别人为工作的人,私下里竟然会如此痛苦。无数记忆碎片在范岳脑中闪回,其中一个画面让范岳大惊失色:那笑星家里,浴室洗手台上摆了好几瓶药,药的样子和范岳在奚志远家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但范岳此时根本没法动弹,也只能硬着头皮看下去,幸好不断的记忆闪回终于快走到终点,马上就是这个笑星最快乐的时刻了。范岳看着那逐渐定格的画面,看着画面中对着洗手台前镜子喃喃自语,苍白憔悴的笑星的脸。那笑星正慢慢说着一个笑话,同时慢条斯理地数着手中的药片。
“有一天,一个人愁眉苦脸地找到大夫,说自己很不开心。”笑星看着镜中的自己,面带微笑说着,“大夫说你不要总是不开心,今晚有国内最出名的小丑来城里巡演,你可以去看看的。”
“可是,那人说,”笑星一字一句地说,“大夫,可是,我就是那个小丑啊!”
“我就是那个小丑啊。”笑星重复了一遍,哈哈笑起来,把手上一整瓶安眠药放下,“演出要开始了,哈哈哈……”
8
范岳一身冷汗,仿佛从噩梦中醒来,终于挣脱了那些幻象。
他抬头一看,却发现面前已经没了奚志远的身影,他心里咯噔一下,即使莽撞如他,也知道自己无意之中犯了弥天大错:那个笑星分明和奚志远一样有抑郁症,而且明显比奚志远严重得多。那么把这个笑星的“开心”渡给了奚志远的自己,到底做下了什么?
他腾一下站起身,大声开口问店员:“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兄弟去哪儿了?”
“出门了。”店员纳闷地看着范岳。
“往哪边走了?”范岳着急地问。
“应该是……海边吧。”想了想,店员不确定地回答。
范岳转身就跑,店员下意识地想拦他,突然停下脚步,挠了挠头,大惑不解,“先付账再吃饭的快餐店,你跑什么……”
9
范岳在寒风中拼命跑着。
海边最高的观景台上,由于天气很冷,地上还有积雪,除了远处一个正翻捡垃圾桶的拾荒大爷,没有别人。奚志远看着远处海平面上星星点点的轮船灯光,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站起身就要往前走。
一只脏兮兮的手拽住了奚志远,他回头一看,原来正是那拾荒大爷。大爷的脸被风吹日晒,黑黢黢的,皱纹遍布,眼神却澄澈干净,“崽啊,你要干啥?”
“大爷,抓住他,别撒手!”远处范岳狂奔而至,一把抓住奚志远另外一只胳膊,这才放下心,咳嗽起来,“老奚,老奚你再给我一天,我错了,这回真是我的错,你再给我一天……”
“范岳,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事我再和你重复一遍,真不怪你。你也别拦我,你今天拦我,不过就是让我多活一天,我真的受够了,每天每天都这么难受,真的……”奚志远噙在眼眶里的泪珠最终还是没有落下来。他轻松地笑着,看准两人现在手松,用力一挣。
拾荒老大爷和范岳同时用力拽住他,两人的手在奚志远背上一碰。范岳害怕奚志远挣扎,另一只手抓住奚志远的脑门,他一只手可以抓篮球,按住奚志远的脑门自然轻轻松松,“老奚,你别这样,你开心点!”
“呃。”奚志远立刻翻着白眼躺了下去。范岳一愣,回头看看拾荒老大爷,看看自己按在大爷脏兮兮手背上的手,又看了看拾荒老大爷的脸。他缓慢地翻过自己的手,那里空空如也,最后一片叶子刺青也消失了。
“……娘的,完了。”范岳只来得及骂了一句,就被连续灌进脑中的幻象弄得失去了力气。
雪花飘落下来。
10
范岳把最后一次借取开心的机会,误打误撞用在了那拾荒老大爷身上。
他心中满是懊悔,可是他知道接下来老大爷的人生幻象会再一次让他失去活动能力,而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接下来的一切。
幻象冲进范岳的脑海中,让他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老大爷的一生不算坎坷,可也不是一帆风顺。有过生离死别,有过刻骨铭心;历经艰难困苦,也有事不由人。可是老大爷一生都开开心心,无论碰上什么,都这么一步步走了过来。
幻象不停变换:老大爷小时候在河滩里和那条吃掉自己几条蚯蚓的鲶鱼斗智斗勇,最后终于钓上来的那一幕,同伴们看着满身泥巴的他,指着他哈哈大笑着;结婚那天,家徒四壁,还年轻的老大爷很难为情,媳妇儿却一把拽过他的衣服,数落着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青梅竹马有多冒失,一边给他衣服打补丁;孩子从小和他一起过得很苦,可他还是能想着办法改善伙食,去变成河坝的河滩逮蛤蟆,串好了给孩子“开小灶”,跟孩子一起笑得开心。
幻象终于要停下,范岳期待地看着,想看看这个一辈子都过得开心的老大爷,最开心的是哪一天。
是今天。
幻象中,老大爷起床,看着堆满垃圾的屋子里,那破成两半的穿衣镜中的自己,笑着开了腔:“老东西,又多赚一天!”
范岳跟着笑了起来。
昏倒在地上的奚志远也笑了起来。
11
三个月后,新学期又开始了。
大学室内篮球场上,范岳运球如风,过人似电,轻巧地晃过两人,一抬手就要把球送进篮筐。
身前有人长身而起,良好的弹跳力让这人仿佛突然长高,手啪一下拍落范岳手中的篮球。
“老奚你个没良心的,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范岳咬着牙怒吼,奚志远嘿嘿一乐,早运球跑远了,“别废话,有本事你也帽我一个!”
奚志远好了,彻底好了。他的抑郁症状一扫而清,海边那天过后,奚志远仿佛大梦初醒一样,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做了几个又累又荒唐的梦,然后反正就想开了。”
范岳也好像成熟了很多,现在说话做事,不像以前那么莽撞了。
以前那些偶尔让他难受的事情,在现在的他看来,都仿佛过眼云烟。
做人,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做大老板也会天天焦头烂额,拾荒老大爷都能天天开心下去。
那他范岳又有什么理由不开开心心地活着?
体育馆外,树上冒出点点嫩叶的绿芽。
严冬过去,春天又要来了。